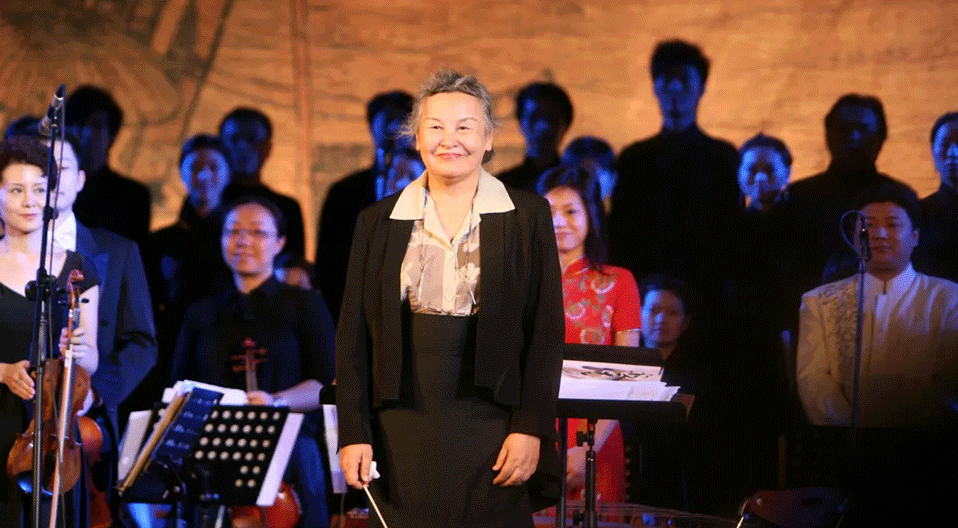
郑小瑛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的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
郑小瑛拿着指挥棒站上《但愿人长久——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指挥台,近二十年的时间一“挥”而过。如今,92岁的郑小瑛依旧矍铄地站在这方指挥台上,正是她对朗诵会的热爱与尊重。“在这个日渐浮躁的社会,唐宋名篇朗诵会的意义不仅是给观众视觉和听觉上的愉悦,更是引导观众们安静下来,体会古典文化的美丽,学会思考,不要畏惧寂寞,慢下来,静下来,这样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
文〡郑小瑛
驱动文化传媒出品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自1999年春节在北京首演,至今已历二十余载,演出近百场,在我国多位杰出语言大师和音乐家的热情参与下,足迹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经久不衰,多年来一直倍受观众喜爱。
唐宋诗词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瑰宝。在当代社会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唐宋名篇”这一融合文学、朗诵、音乐为一体的艺术精品愈发散发出其独有的魅力。
把音乐跟古典诗词结合到一起,这个创意很了不得!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因为它的音乐不是一般有点动静的背景音乐,而是融入到了这首诗词之中,所以我说它是“诗中有乐,乐里有诗!”诗词诠释了音乐,让音乐具象化了,而音乐又升华了诗词的语境,强化了诗词的戏剧性!
由于节目策划人钱程邀请了多位作曲家参与这个工程,因而这场音乐会的风格也是缤纷多彩,各有千秋的。你会欣赏到三种不同的体裁:有诗词朗诵与配乐,有诗词独唱,还有诗词合唱;这些丰富的形式也给古典诗词注入了新的活力,给观众们带来了崭新的艺术享受。
诗词朗诵与配乐
比如:当时还很年轻的著名作曲家叶小纲为李白《将进酒》谱写的音乐,由定音鼓一阵狂野的敲击转入兴奋而执着的心跳;接着,音乐像一阵清风掠过,你才听见了那醉汉的心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时,汹涌澎拜的黄河,好像就在你眼前!然后,一段由竹笛和琵琶加钢琴奏出的调性模糊的音乐,伴随着晕晕乎乎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朗诵到“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作为呼应,乐队响起了一段优美的旋律,最后“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诗人激动的情绪与乐队庞大的热流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整体的高潮!突然,一切安静,又听见了诗人再次肯定地,坚信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乐队——仓!这里诗句与音乐之间巧妙的戏剧性配合是作曲家都设计好了的,而能否配合得恰到好处,就要看朗诵者和指挥之间的彼此理解和默契了!
我国著名民乐作曲家,指挥家顾冠仁为白居易“琵琶行”朗诵的谱曲,古朴抒情,也是丝丝入扣地配合着诗句的内容和感情的起伏:比如观众会先听到优雅的琵琶声,才与诗人一起“忽闻水上琵琶声—”,先听到了琵琶激动的弹奏,诗人才点拨似地念道“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音乐逐渐平静、噎息,长时间死一样的沉默—配合着“此时无声胜有声”!接着缓慢优雅的音乐轻轻伴随着琵琶女对自己生平的倾诉, 直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音乐才热烈地奏响,这强烈的音流大大加强了诗人与琵琶女共同命运的呼唤!最后琵琶与小提琴清淡而意境深远的二重奏,更是催人泪下地伴随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每个段落,甚至每个句读,经过音乐与朗诵的贴切配合,大大增强了这篇叙事诗感人的抒情性。
诗词独唱
青年作曲家刘长远为男中音独唱与合唱写的张孝祥的《过洞庭》,又是另外一个风格;低音弦乐在稳定而淡然的节奏里轻轻拨弄,伴随着一曲优雅的笛声,好像诗人在平静的洞庭湖上,“扁舟一叶”,“表里俱澄澈”的坦荡胸怀;这曲是由我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演唱的,他浑厚的音色,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慷慨高歌、大声朗诵,伴以轻轻的合唱,感人至深。
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为吴文英的《唐多令 · 何处合成愁》的谱曲,被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演唱得动人心弦。这首朴素却暖心的旋律完全不是花腔女高音可以炫技的曲目,然而它由竹笛,磬铃、竖琴和弦乐轻轻铺垫成的背景,让歌者自然地投入到那个“愁”字的意境中去,它也已成为歌唱家心爱的一首保留曲目了。
诗词合唱
我国老一辈音乐家青主为苏轼的《念奴娇 · 赤壁怀古》谱曲,由著名女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了大合唱;早已是一首我国优秀的合唱经典了。那恢弘雄伟的气魄,深沉如梦的音调,极好地刻画了词人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敬仰,和对自己坎坷人生的叹息,最后无比感慨“人生如梦”后,昂然一声:还是痛饮一杯吧!
著名作曲家莫凡为白居易的《长恨歌》的谱曲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它极好地配合了这首长诗的戏剧性。比如一开始抒情的音乐伴随着“缓歌漫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紧张的琵琶和打击乐预示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凄凉的琵琶独奏伴随着“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以及用板鼓孤独的击打和竖琴的刮弦,描绘了帝王返宫后见到“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的冷落景象;“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在竖琴,钢片琴叮叮咚咚的伴奏下,我们也进入了蓬莱仙境,最后“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带来了与管弦乐交织在一起的倾诉爱情的最高潮!
这个有些另类的音乐形式,首先是给每演一次都要临时组织一个相应乐队的主办方带来了不少麻烦。由于10来部作品出自10来位不同作曲家的笔下,并没有事先约定的乐队编制规范,于是乐队有大有小,加入管弦乐队的民族乐器也是五花八门,表演的难度还相当大,因此每到一个城市演出都要物色到足够优秀的乐手,还得有足够的排练时间,这就给组织者增添了不少成本和困难!
对于音乐指挥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朗诵者的速度会因人应时而异,并不像歌剧和协奏曲的演员那样,他们的表演,都在乐谱的要求和指挥的掌控之中,于是我不得不把所有的诗词按照大致出现的方位抄写在我的总谱上;当朗诵进行时,我必须用“第三只眼”紧盯着诗词,带着庞大的乐队有表情地,时快时慢地伴随着朗诵,或者在演员偶尔发生漏词或不寻常的险情时,快速调整我的速度,救他一把,才能保证这个综合性艺术表演的完美!这也是观众看不到的,对指挥的敏感度和掌控乐队能力的另一种挑战!
因此,每一次看起来“天衣无缝”的配合,既体现了朗诵者在尽情投入表演的同时,还必须理解音乐是在衬托他,因而他必须要记住一些与音乐呼应的节骨眼,而音乐家们也会随着演员情绪的起伏跌宕,积极领会和巧妙融入;在陶醉了观众的同时,表演者们也获得了成功艺术合作的满足。
出于对这个音乐会的喜爱,我曾在20多个城市指挥演出了这套音乐会近50场,每一次合作对我都是一次机会难得的,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反复学习和体验,以及对各位语言大师艺术造诣的零距离享受!
我爱“唐宋名篇”,也爱坚持这个巨大工程的,台前台后的每一位参与者,相信它将成为一部传世的经典!
///
ID:Propel Media